

正在建设“三城三都”(世界文创、旅游、赛事名城,国际美食、音乐、会展之都)的四川省省会成都,既是一座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中华优秀文化的区域分支古蜀文明)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座自然条件优越、富有浓郁地方特色,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闪烁着魅力之光的大都市。
说成都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于这里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在商代就出现了独具特色的西蜀文化。从宝墩遗址到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富有区域特色的文物,此后直到近代,四川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成都自然条件优越,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带,“二龙”(龙泉山、龙门山)环伺,二江环绕,沃野千里,气候宜人,水旱从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说成都富有魅力,是因为从公元前4世纪古蜀王朝开明第九世决定迁都成都以来,成都建都、得名2300余年不变,是中国地名得名史上第二古老的城市。成都拥有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等名胜古迹,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其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吸引了大批文豪墨客源源而来,汇聚于此,形成了“自古诗人例到蜀”的文化现象。因此,成都文化发达,文物鼎盛。说成都是闪烁着魅力之光的大都市,在于从公元前4世纪的古蜀王朝定都成都以来,这里是蜀汉、成汉(氐人政权)、前蜀、后蜀等多个地方政权的都城,也是各大一统王朝的州、郡治所之所在。成都在汉代“名列五都”,晋代文学家左思《蜀都赋》赞叹其“既崇且丽,实号成都”,唐代获得“扬一益二”的美誉。诚然,成都华丽异常,天然优美,在中国很难再找出一个像成都一样的古都。
从三四千年前开始,以成都为中心的地区成了古蜀民众生产、生活最重要的区域。古蜀民众在此繁衍生息,创造出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等一脉相承的区域文明,此后,鳖灵、李冰等在此治水,发展经济,开启了成都作为“古都”的悠久历史。
秦汉时期,成都被纳入中原文化的发展体系,在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下,成都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商业规模、城市格局不断扩大,成了与临淄、洛阳、邯郸、宛等相媲美的“五都”级全国性中心城市。无论是张骞在西域大夏看到的当地畅销的“邛杖”“蜀布”,还是唐蒙在南海之滨番禺吃到的“蜀枸酱”,这些代表了大汉强盛的“中国造”,实则均是地道的“成都造”。文翁、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文人、学者,极大振兴了这座城市的文教之风,增添了这座名城的风雅之气。
两汉交替之际、三国魏晋南北朝之时,中国或短暂或持久地进入了动荡年代,各大政权间的兼并割据时有发生,成都受到战争破坏程度较小,因而在乱世中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常璩等文史巨匠继续书写着文化古城的辉煌。
隋唐五代时期,成都的城市规模较前代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以蜀锦、蜀布、蜀纸、蜀茶等为代表的产业带动了成都手工业经济的发展。陈子昂、薛涛、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或是川人,或者入川居住,书写着“自古诗人例到蜀”的传奇。
宋代,成都人文鼎盛,造纸、雕版印刷业发达,依然为全国重要的商业中心,有着“西南大都会”“天下名城之冠”的美誉。魏了翁等理学名家辈出,环成都地区则涌现了眉州“三苏”、井研“四李”以及张栻等文化巨人。
到了明清时期,成都更是成为外来人口汇聚的天府乐土,移民的大量涌入也让成都的文化呈现出乐观包容、时尚优雅的独特性。
司马迁《史记》曾言:“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语虽是记述舜的事迹,但宋人已化用此语来解释成都城市名称的由来。如乐史《太平寰宇记》中称:“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的确,任何一个聚落或都城的形成都绝非偶然,自然地理条件的好坏是人们选择居所的首要标准。成都从战国时期开始,历经2000多年,城址未变、城名未改、中心未移,富丽繁荣,闻名遐迩,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成都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文物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各种各样的文物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状况。成都素称人文城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文物,透过这些文物,我们可以窥见祖先们的智慧和经验,也可以总结勾勒历史演变的轨迹与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成都文化,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天府文化,为新时期成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近年来,成都考古蓬勃发展,重要考古发现频出,这些对于认识古蜀文明及成都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016年,成都博物馆新馆在天府广场西侧顺利落成,这使得成都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犀牛、都江堰发现的李冰石像等珍贵文物,再现了战国时期成都在经济社会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王国维先生指出研究历史“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这就是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只有把发掘出土的文物和史书典籍的记载相互验证,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历史信息。古书典籍中记载了先秦时期古蜀国历经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时期,而考古学家在成都及其周边发现了宝墩古城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遗址等多处先秦时期重要的遗存;《华阳国志》中有李冰治水“作石犀五头以镇水妖”的记载,而天府广场东北部出土了千年石犀。此外,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模型反映出两汉时期成都纺织业的发达,“锦城”“锦官城”的机杼声似乎回荡耳边;出土的众多汉代说唱俑则反映出成都民间艺术的盛行,面容可爱、动作滑稽的伶人再现了成都作为休闲之都的历史片段。诸如此类的文物不胜枚举,如见证了医学盛况的经穴漆人、记载了“列备五都”的东汉石碑、表现了大唐乐舞的永陵乐伎浮雕、印证了蜀学成就的后蜀石经等一系列的考古文物,都是成都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
本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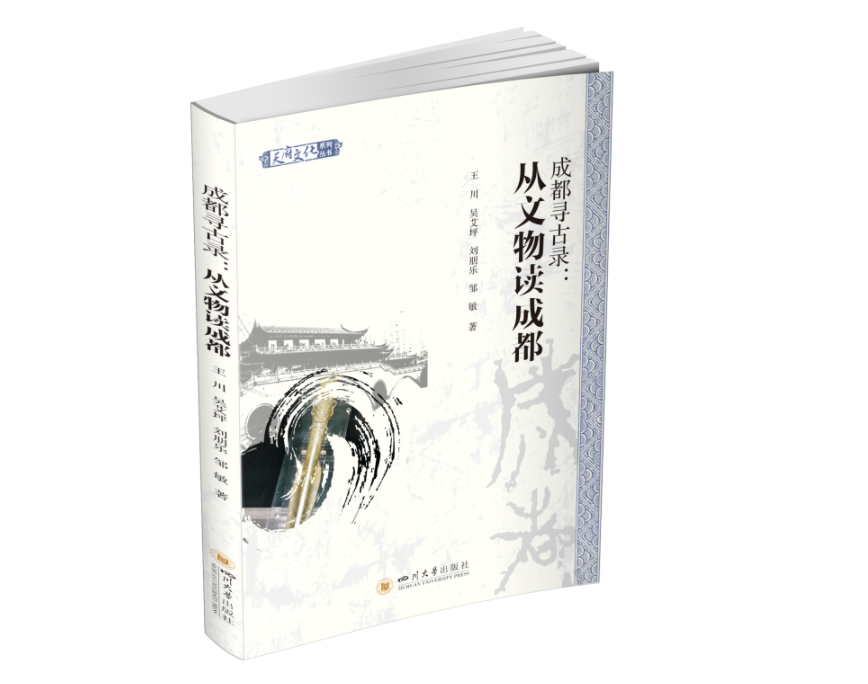
《成都寻古录:从文物读成都》
王川 吴艾坪 刘朋乐 邹敏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名为《成都寻古录》,意在成都寻找文物的踪迹,跟随文物的步伐探寻成都历史发展的脉络。作为一部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本书选取的文物多为近年来成都地区发现的代表性文物,大多耳熟能详。通过介绍文物发掘的历程,引出文物背后的故事,进而为大众了解学习成都的历史知识提供参考。
本书参考了《四川通史》《四川简史》《成都通史》《成都历史文化大辞典》《成都简史》《成都街巷志》等著作,采纳目前基本上是定论的成果,力求知识层面的准确可靠。同时,为了满足不同文化群体的需求,本书还参考了部分报纸杂志和网络资料,行文尽可能保持通俗易懂的风格。作者将本书所参考的资料附于书后,以供读者查阅。
本书通过文物实证成都古史。王国维先生倡议“二重证据法”,徐中舒先生倡议“三重证据法”,均强调对于实物的重视。蔡鸿生教授在授课时,常以“文献与文物相结合”“见物与见人相结合”相教诲,这对于本书的撰述启发甚大。因此,作者利用各种渠道,极力搜集各方文物照片,并得到了成都博物馆馆长李明斌研究员等多位学者、多个单位与友人的慨然相助。除了成都博物馆等单位提供的文物照片之外,本书还增加了能够反映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图片。
作者简介

王川
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院长、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入选者,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第五届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2018-2022)委员,兼任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等职。
吴艾坪 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
刘朋乐 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
邹敏 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书试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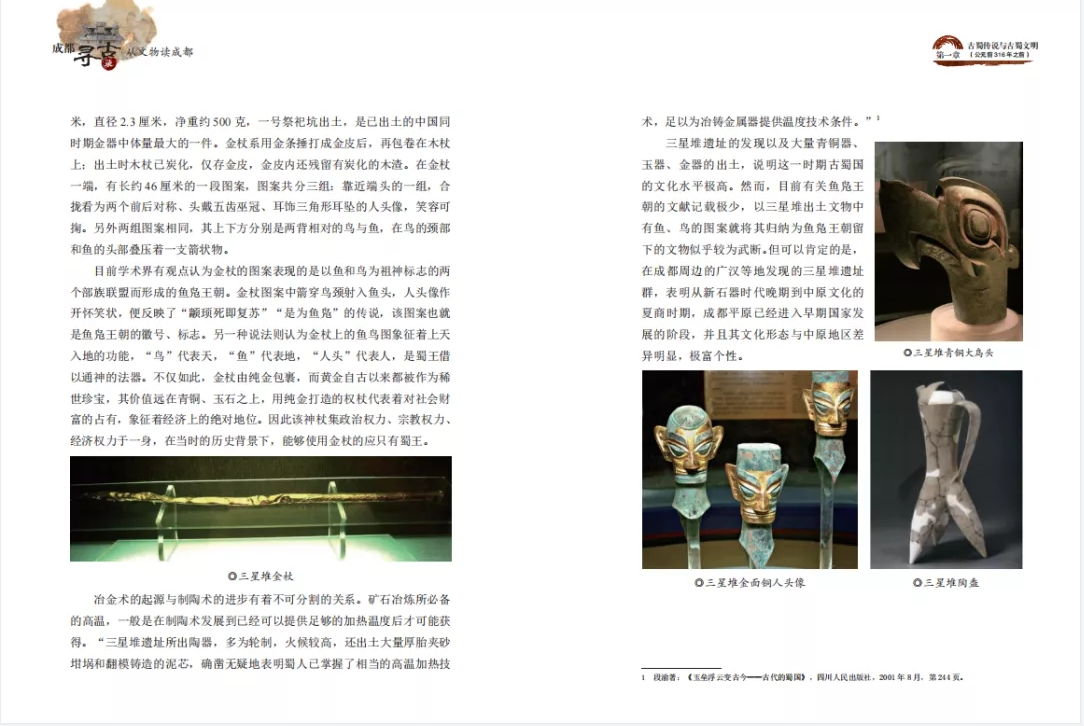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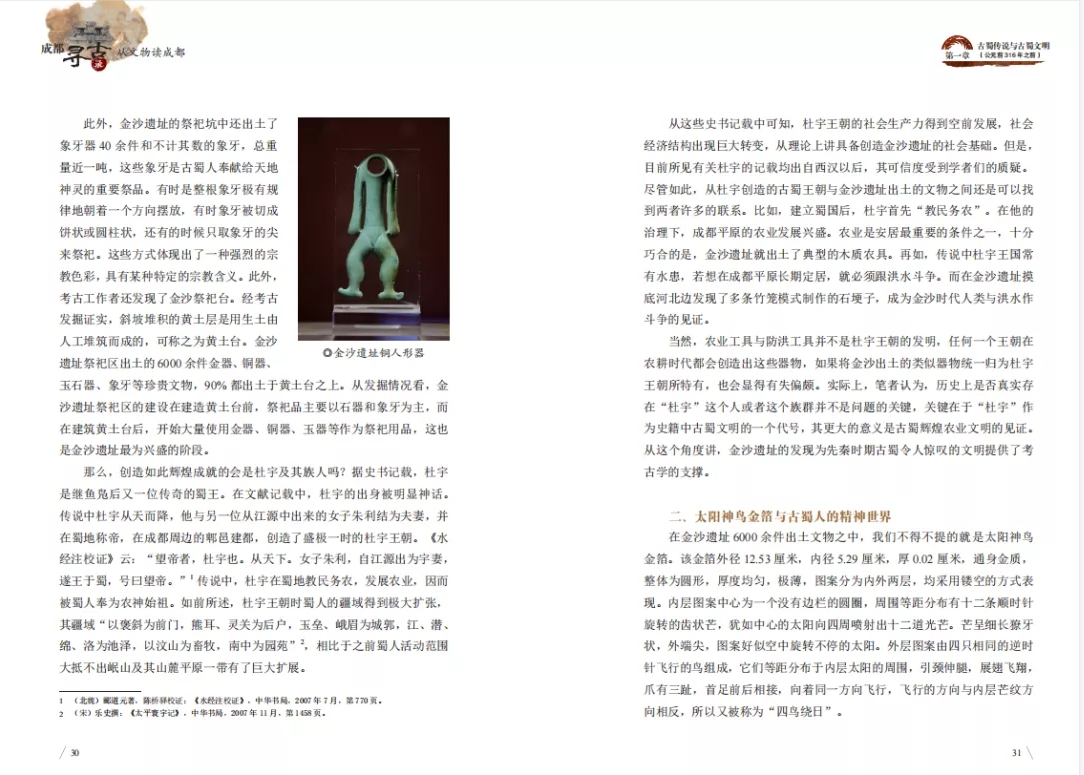
编辑:中华传统文化学院
地址:(狮子山校区)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5号 (邮编:610066) (成龙校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二段1819号 (邮编:610101) © All Right Reserved . 四川师范大学 版权所有 (四川师范大学网信处制作维护) 蜀ICP备05026983号 信息管理 |